學術交流
研究 | 胡斌:跨歷史與跨文化視角的中國美術現代化研究斷想(一)

圖1 《新青年》第6卷第1號,19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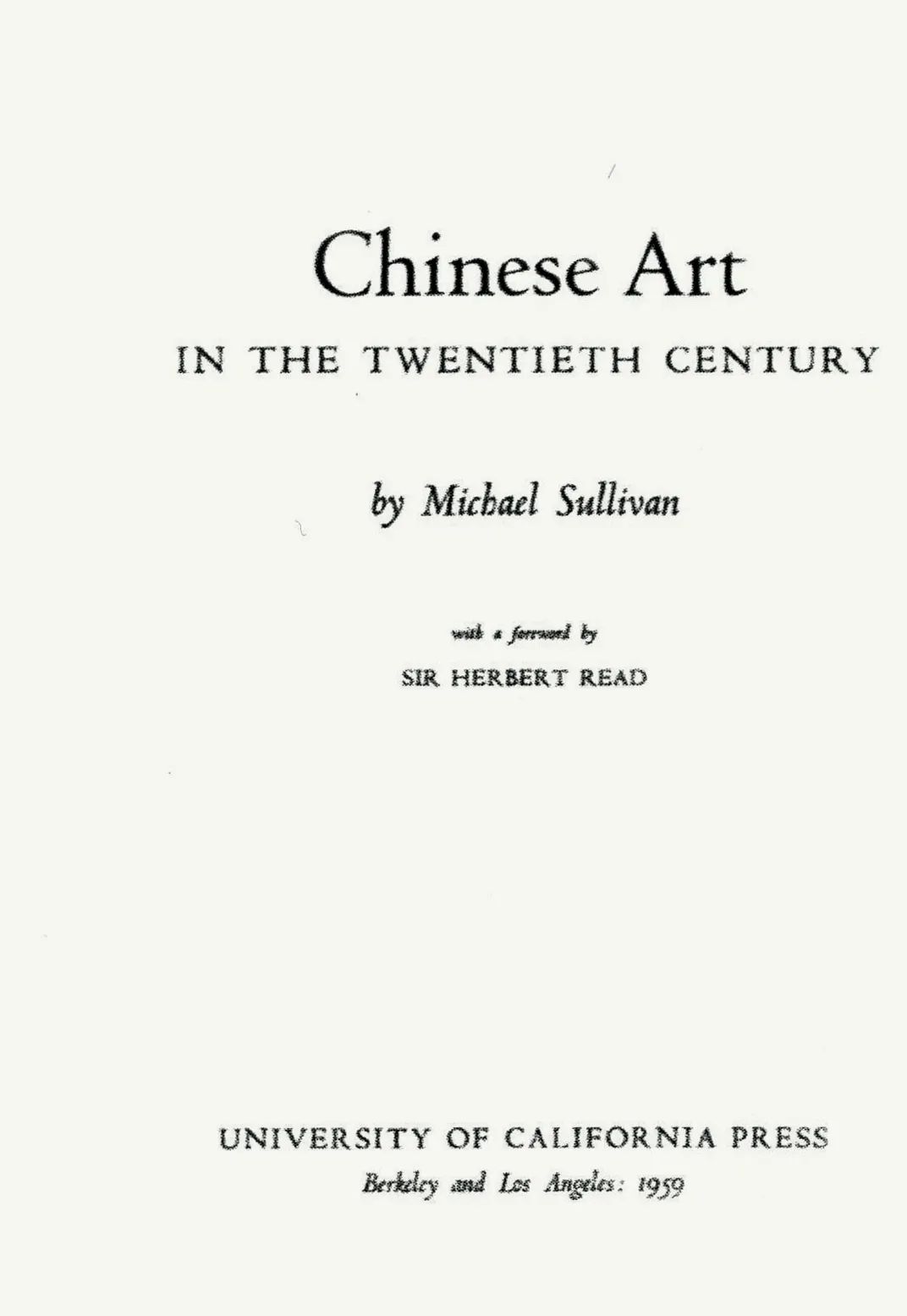
圖2 [英]蘇立文《20世紀中國藝術》,19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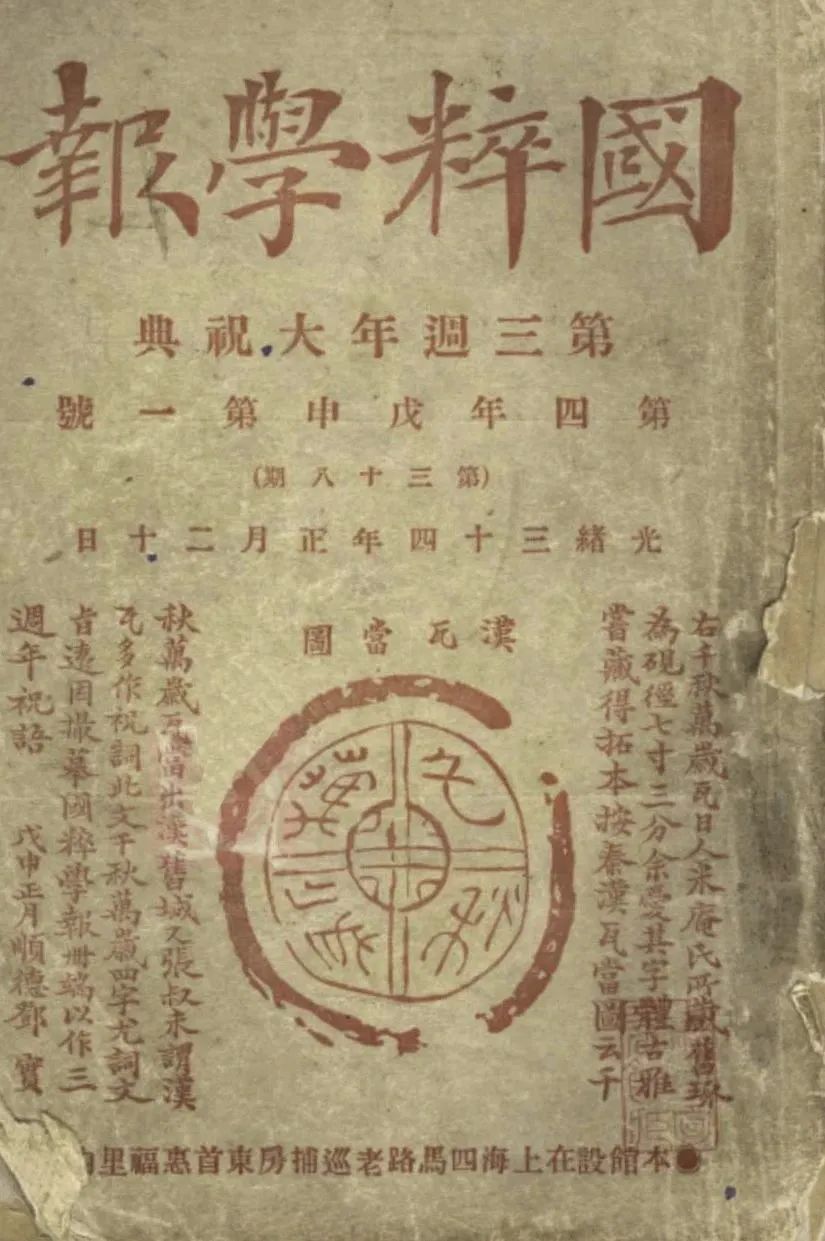
圖3 《國粹學報》1908年第1期

圖4 龐薰琹《盛裝》紙本水彩 1942年 中國美術館

圖5 蘇天賜《藍衣女像》布面油畫 73cm×51cm 1948年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美術雜志社
(上述文字和圖片來源于網絡,作者對該文字或圖片權屬若有爭議,請聯系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