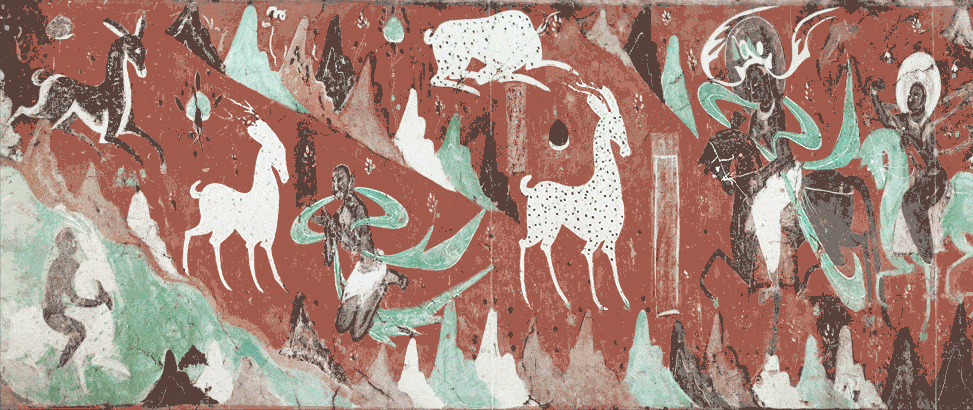紀念 | 常書鴻:敦煌飛天壁畫是世界美術史上的奇跡
敦煌石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根據記載,一位名為樂僔的和尚在沙漠中行走時,忽然見到天邊金光閃耀,就像是萬佛出現,于是樂僔就在附近的巖壁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這也是莫高窟的第一個石窟。后來人的修行人和信眾們也陸陸續續在這里開窟修禪,一直持續了千年的時光。
敦煌歷代壁畫,包含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貫穿敦煌飛天的演變史,講述了飛天起興、創新、鼎盛、沒落階段的完整歷史,展示敦煌歷代飛天的藝術風格,讓讀者感受敦煌藝術的豐富、博大之美。
隨著佛教的傳入也傳入了印度佛教藝術的圖像。飛天,就是佛教圖像中最令人喜愛的形象。在印度,梵音叫她犍達婆,又名香音神,是佛教圖像中眾神之一。她出現在樂鼓齊鳴、天花亂墜的佛說法的莊嚴時刻。她們居住在風光明媚的天宮十寶山中,不食酒肉,專釆百花香露,散天雨花,放百花香。《觀無量壽經》描寫佛國凈土時說:
如一念頃,即生彼國七寶池中,……行者身作紫磨金色,足下亦有七寶蓮花……經于七日,……即能飛行遍至十方。

莫高窟第172窟 北壁 觀無量壽經變 孫志軍攝影(敦煌研究院供圖)
這說明飛天和西方極樂世界的往生靈魂一樣,誕生在七寶池中,她們也都是蓮花的化身。敦煌莫高窟第257窟北魏背光畫中的兩個蓮花化生,就是往生靈魂的雛形。
從鄯善沿著天山南路東行大約三四百公里,就到達了玉門關內的敦煌莫高窟。這個地處河西走廊盡頭的塞外江南,從歷史和地理上考察,它和天山南路的于闐、鄯善等地的關系是比較密切的。5世紀高僧法顯的西游,就是從敦煌經米蘭(鄯善)、于闐并在那里參加祇園盛會的。
自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建立河西四郡后,敦煌就是一個總綰東西“華戎所交”的都會。隨著政治、經濟的發展,文化也有了一定的發展。敦煌漢代就有著名的書法家張芝,晉代有索靖及沙門竺法護,南北朝有劉昞,隋朝時有薛世雄,等等,都是歷史上文藝、政治、宗教方面的頭面人物。
這一切都說明敦煌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也說明敦煌藝術源遠流長,因而敦煌飛天才具有迷人的魅力。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壁畫中,就能看出顧愷之的筆墨遺風。同樣,從他的名作《女史箴圖》表現的長裙曳地、迎風飛動的垂飾以及氣韻生動的風格,也顯示出中國古代繪畫傳統對敦煌飛天藝術的影響。
當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時,正是耶穌誕生前一個世紀的時候,東方和西方兩大世界性的宗教正在興起。印度和中國信奉大乘佛教,西方拉丁世界信奉基督教。這兩大宗教雖各有各的教義, 但兩種宗教同樣含有救世濟人、慈悲為懷的共同愿望,都需要運用文學藝術中最有感染力的方式和雅俗共賞的圖畫、語言,使迷信與幻想蒙上一層善與美的輕紗,配以動聽的贊歌。而敦煌飛天,正是這些藝術贊歌的優美插曲。
從印度傳來的佛教犍達婆(飛天),上身赤裸,在舞帶飄忽中做出凌空飛舞的姿態。鳩摩羅什在公元416至417年譯成的《妙法蓮華經·譬喻品》中,有關于裸體飛天的一段描述:
爾時四部眾比丘尼、優婆塞……乾闥婆(即飛天)……見舍利弗于佛前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中歡喜踴躍無量,各個脫身上所著上衣,以供養佛。
這就是飛天袒衣露胸的依據,同時也證實了,當時中國佛教的圖像已突破了封建社會衣冠周正的習慣。自此以后,我國新疆、敦煌、云岡、龍門等地,在四五世紀差不多都出現了袒衣露胸的菩薩和飛天。
飛天,是浪漫主義思想方法與創作方法相結合的產物,是古人最善良、最美麗的理想憧憬的進一步飛騰與升華,而敦煌則是飛天的薈萃之地。莫高窟492個洞窟中,有270多個洞窟繪有飛天,總計4500余身。其中僅第290窟就有154身各種姿態的飛天。盛唐第130窟中有身長2.5米的飛天,也有不到5厘米長的飛天。
這些飛天圖像,不受造像度量經的約束,千變萬化的姿態,隨意畫在洞窟內較高的壁面。她們被畫在窟頂藻井圖案的四角、藻井中心部分、藻井垂幔的四周、佛龕頂部、佛說法圖上方、佛故事畫的上方、窟壁上部周邊等處。飛天飄游在西方凈土變的上空,穿行在樓閣門扇窗框間、佛說法的背光中。她們配合整窟壁畫,起到裝飾美的作用,豐富了“天衣飛揚,滿壁風動”的意境。
 莫高窟第329窟 窟頂藻井 飛天蓮花藻井 吳健攝影(敦煌研究院供圖)
莫高窟第329窟 窟頂藻井 飛天蓮花藻井 吳健攝影(敦煌研究院供圖)
敦煌早期的飛天繪畫,代表了藝術匠師們擺脫了漢魏以降傳統禮教的束縛,馳騁他們的幻想力,是具有浪漫主義風格的偉大的創作。“飛”表示他們精神的解放,是早期藝術風格的特征。豪放的筆力,對比的色調,在行云舒卷、流水有聲的畫面上,傾吐了千百年被壓迫、被屈辱、被歧視的敦煌古代無名畫工們發自內心的呼聲。
北魏時期的飛天,可以明顯地看出兩種風格。一種仍保持濃厚的西域風格,筆觸粗健豪放,體態野獷簡單。在大紅底子上著灰(這種灰色是銀朱混合色年久所變的)、石青、石綠、黑、白等色烘染。另一種顯然是從中原傳來的風格,飛天臉形修長,飄帶尾部鋒利如削,飛行動作雖然加強了,但是不能輕盈自如。還有一種畫在背光中的飛天,她們配合背光向上趨勢的火焰,一身接一身地向上飛翔著。
敦煌莫高窟有西魏大統四年(538)、五年(539)題記的第285窟,這個窟頂繪制了伏羲、女蝸、日天、月天,還把靈鳥、怪獸、風伯、雷神畫在天花與流星、行云之間。在這滿壁風動的天空中,還穿插有身材比較苗條細長、飄帶翻卷、瀟灑的飛天,她們已粗具顧愷之《女史箴圖》的“骨法用筆”“氣韻生動”的流韻。該窟南壁得眼林故事畫的上方,配置了一條6米多長、一氣呵成的12身俊秀美麗的伎樂飛天,這是莫高窟飛天的一幅劃時代的杰作。從此使北魏以來帶有天竺石刻菩薩那樣壯實飛天的造型,變成晉顧愷之那種秀骨清像、體態婀娜的風姿。
這一時期的飛天畫在行云流星中。云氣紋伴隨飛天,千變萬化,以至天衣與云氣達到魚水難分的地步。這12身伎樂飛天,她們演奏著琵琶、箜篌、鼓、簫、笛、笙、排簫等。這些飛天繪制在天花亂墜的明亮白堊底色上,配以鈷藍、石青、石綠、朱砂、黑等色,并用朱紅及墨線勾勒,其用筆之流利婉轉,與其說是出自高手的神筆,不如說是春蠶吐絲。
在那12身優美的伎樂飛天中,奏箜篌的飛天正在安詳自然地揮動纖巧的雙手,彈奏出清脆悅耳的樂聲,似美玉碎裂的聲音,又像鳳凰的鳴叫,似帶露的荷花在低怨,又像芳香的蘭花在縱笑。那手執琵琶的飛天,好像正在構思一曲新穎的“琵琶行”,用白居易的詩句去披露她胸中的構思,一定相得益彰。“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她使我們迷離恍惚地沉醉在不盡的聲韻中。
隋代的藝術匠師們,像鑲嵌金銀做的器皿一樣,用絢爛的色彩描繪流云般的卷草紋、聯珠紋和對獸紋等,更增加了隋代飛天的華美。隋代飛天的身軀,畫得比較靈活,配合飄帶所占的空間比北朝的大。飄帶曲折翻卷,加上大動作的舞姿,顯得動感較強。再配以波浪形的五彩繽紛的唐草卷葉,推波逐浪,使飛天和花草行云都在用同一個速度流轉運行。有的飛天緊貼藍天,好像不是在窟壁上飛行,而是在浩瀚無垠的太空中疾飛速翔,勢如流云飛度,花隨人舞。
尤其新穎的是,第407窟隋窟藻井,在華蓋圖案中心,繪制了一朵豐碩的蓮花,花心有三只兔子向一個方向奔跑,三只兔子只繪了三只耳朵,每一只兔子借用另一只兔子的耳朵,這是藝術匠師多么巧妙的創作!更精彩的是,在這蓮花周圍藍紋的底色上畫了8身飛天,在彩云飛花中追逐飛繞,栩栩如生,生意盎然。

莫高窟第407窟 窟頂藻井 三兔蓮花飛天井心 張偉文攝影 (敦煌研究院供圖)
從公元618年起,歷時將近300年的唐朝,是我國封建社會文化藝術的盛世。從“貞觀之治”開始,總結了歷代藝術的創作經驗,保留了北魏拓跋族所特有的粗獷有力的筆調和中國畫史上顧愷之、陸探微“跡簡意淡而雅正”的風格,并通過絲綢之路和往來敦煌古郡的旅客吸取了伊朗薩珊王朝細密精致、色彩瑰麗的紋飾和印度3世紀阿瑪帝時代石雕造像那樣肥碩生動、富有肉感的人物造像等因素,改變了過去六朝造像秀骨清像的時代特征。人物造型開創了張僧繇“面短而肥”的楊貴妃式唐代美人的豐腴圓潤風格。
這個時期的飛天,面形豐滿圓潤,體態婀娜多姿,臨風飛舞,像我們時代在外層空間的航天人,在失重的情況下自由自在地輕輕飄浮在天空彩云間。由于初唐到現在已經經歷了1300多年的歷史,飛天赤裸上身的顏色,由原來的銀朱和白粉氧化變成棕黑色。
第321窟與第320窟黑飛天是敦煌飛天美中之美的代表。她們是剛從天宮憑欄伎樂群中投身下凡的天女,是敦煌古代匠師們精心刻畫出來的造型。看到她們伸展自如、婀娜多姿的體態,我們不禁聯想到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波提切利所畫的《維納斯的誕生》等馳名世界的杰作。敦煌無名的藝術匠師們和佛羅倫薩的藝術大師們一樣,他們在安排自己所創作的優美飛天伎樂時,注意與周圍宗教氣氛相和諧。
僅看一下第321窟黑飛天的手臂處理和天宮諸憑欄菩薩像舞蹈一樣的手勢、身段與動作,一定會使你嘆為觀止。這些憑欄菩薩和下降飛天,都具備著宗教一般深情而無邪的神秘的愛撫。敦煌古代的藝術匠師們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手法,成功地表現了香音神一塵不染的宗教情操,提高到超人的幻境中,給人以完美的藝術享受。
敦煌壁畫的主題是根據佛經內容而定的。敦煌石窟藏經洞中發現了不少阿彌陀凈土經。將佛經內容用圖像故事畫在壁上的,就叫作“變相”或“變現”。把《阿彌陀經》主題用圖像故事畫在壁上的,就叫作“阿彌陀凈土變相”,或“阿彌陀經變”,或“西方凈土變”。這個變相的內容,是“彌陀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
飛天就是在天花亂墜的釋迦牟尼佛說法時出現的。她們有時出現在池角水邊,有時出現在天宮的樓閣中,有時又從亭角的窗戶中穿梭似的往返上下飛舞。使我們驚異的是,飛天的飛翔并不是靠翅膀,而是靠迎風招展的幾根彩帶,是用線表現出來的飛舞。這就是畫史上所說的吳道子線描式的飄帶迎風飛舞的“吳帶當風”。敦煌唐代飛天,正是乘著當風的“吳帶”而生動活潑地飛翔起來的。
在中國美術史上,人們一貫用“曲鐵盤絲”來形容晉代畫家顧愷之的有力線描,用“春蠶吐絲”來形容吳道子的行云流水般的線描。敦煌飛天發展到像顧愷之線描的堅實,像吳道子線描的連綿不斷,從而構成了中國佛教藝術在敦煌杰出的創造性成就。
在從北魏到隋唐的發展過程中,曾經有一段時間,印度佛教藝術受到來自西方犍陀羅式的希臘藝術的影響,有所謂犍陀羅希臘-印度佛教藝術。他們表面上模仿漢代的線條,實際上都是希臘時代遺留下來的呆板線條,有所謂曹仲達的“曹衣出水”式的平行衣褶上的線條,這就形成了佛陀袈裟的寬袖大袍。它不只包括了印度民族生動活潑的石雕藝術的優良傳統,也使印度早期石刻飛天成為沉重不能上升的藝術形象。
直到4世紀的阿瑪爾筏帝時代,才擺脫了犍陀羅式,而創造了豐碩圓潤的印度阿旃陀時代的民族人物造型。這也很類似敦煌飛天藝術擺脫了北魏粗獷時代,而達到隋唐的民族傳統發展時期。
到了五代、宋、元時代,像初盛唐那樣依靠飄帶起舞的飛天少了,而是襯托一堆云氣表示飛行,因此“吳帶當風”那樣輕身起舞的飛天少了,飛天的造型也變得比較笨重了。這時的飛天造型,下面托著一大堆卷曲式的云層,裝飾性強了,但飛天臨風起舞的印象淡了。到了西夏及元代,大概蒙古和西夏民族已沒有隋唐的清秀婀娜,飛天的風格也變得像明朝重床疊屋的藝術風格了。

常書鴻(1904—1994),著名畫家,敦煌藝術研究家,我國敦煌學的奠基者和敦煌文化事業的開創者,被譽為“敦煌守護神”。1927年赴法留學學習油畫,作品屢獲大獎,并被法國國家博物館收藏。因在書攤偶遇《敦煌石窟圖錄》,決心放棄巴黎的舒適生活,回國投身敦煌石窟保護工作。1942年參與籌備敦煌藝術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長。1949年后歷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國家文物局顧問、甘肅省文聯名譽主席。
原文載于:絲路書院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