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杭間:寄予希望的設計——超越日常性(一)

1
日常生活是多元復雜的,我們總是想到從某個專業的角度出發,按照慣性思維去思考“日常性”。實際上所謂的專業,是基于社會普遍的知識上升到一定程度,類型化或體系化后,才形成專業。專業本身離不開專業“形成之前”的知識背景,因此,從怎樣的專業立場來討論日常性的問題尤為重要,對最顯現日常生活技術和文化表征的“設計”來說,尤其如此。
人的日常生活,今天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快速發展的技術使社會、生活、社區、情感、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原來是傳統社會的個人生活與思考,現在已經由那些當代技術社交媒體平臺,變成了全民的生活交流與思考。傳統生活時代,我們很難如此迅即看到他者的生活與困境(民間傳聞和印刷書籍的傳播是多么緩慢),而現在“環球同此涼熱”,資訊因網絡與數字化生活而即時進入大眾生活,甚至能裹挾大眾的喜怒哀樂。在知識通過網絡平臺、AI技術建構的“云”世界中,全民似乎進入一個人人知道的“常識”時代,人們從日常生活的體驗或旁觀他人的生活來切入并塑造自身的標準和價值,并認為自己站在時代的前沿。因此,日常性涵蓋了社會和專業兩者之間的所有社會生活,即使是專業,也已溶解在日常生活中。“設計已死,只有服務”,設計師不能脫離提供服務的具體日常生活——雖然那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真實的日常生活。
關于對日常生活及其審美化的反思,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以及后現代西方的思想家們,有豐富的思考,并對專業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正因為他們是站在超越所謂的專業角度來思考問題的。
科學理性假設世界是理想的勻質化模式,以邏輯追問的方式對待自然,成為近代科學的一個基本態度。理性“迫使”自然說一些“純客觀”的答案[1],然后再用它來解釋或指導日常生活。不僅是自然科學,現在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如此重視學科建設(人文的社會科學化)。使人不安的是,這種理性的建構態度,其實離開了各種具體情境以及人類主觀的差異,而這些才是日常生活價值的核心所在。它們在各種事件的內核中呈現,在現代生活中表現為一個世俗化的過程與經驗體系的升華。想想那些古老的學科,如植物學、中醫藥學等,當年李時珍《本草綱目》是怎么完成的?一個人在有限的一生中是如何綜合前人的成果,將近二千種藥物進行分類辨析,現在想來都覺得不可思議。植物學在漫長的歲月中,在一代代人對植物發現、嘗試的基礎上,慢慢了解它們的性能,這些經驗長期積累,逐漸形成理論體系和敘述體系,從實踐變為普遍的知識,被大家接受以后,再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常識。許多其他民族也都有他們的傳統醫學,以及其他傳統知識與技能體系。在過去,這些都是基于經驗主義。現代醫學是實證性的,在嚴格的實驗、量化、提純等基礎之上,并基于人類共通的一些標準,但對于不同族群,甚至同一族群的個案,也都有差異之處。日常生活對醫學的反饋也是同樣,基于經驗主義與具體情境的反饋,對個體而言,這些復雜而豐富的經驗與體驗,正是學科專業進步的階梯。

日常生活的文化復雜性遠不止于此,例如:什么是中國文化?歷史上中原政權不斷地與北方、西北方的游牧民族產生交匯,漢族也被其他民族統治過,直至晚清的西學東漸等,但中國文化的核心傳統都得以保持。如何保持并不是抽象的,中國傳統文化中來自東亞農耕文化所產生出來的天、地、人那種以經驗為基礎的系統性思維理論,仍是中國文化的主流。這個“經驗”就是日常生活——在漫長的日常中,通過衣食住行,對這些思想產生了潛移默化的交融與凝聚。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經驗主義,以及重倫理和體會式的思想,是對我們日常生活行為的提煉,也是指導行為的重要理論依據。它們之間的關系,有大地物候賦予的難以改變的邏輯,這也許正是中國文化不被同化的重要原因。
人類的知識則開始出現這樣的趨勢:單一的學術在解體,變得愈加融合。單一知識體系的專家在消解,人類的知識——原來的分學科的知識和未來通過人工智能介入的科技文明體系,會形成伴隨日常生活的新的方向。我們是否會重新尋找一種感性的聯系,回到日常生活中人類基本的情感,尋找那些經過漫長的時間,仍具有巨大共情的力量,這種感性的因素和情感價值在今天恰恰可以平衡諸多矛盾。這個判斷也可以延伸到設計上,無論是社會對日常生活和設計關系的理解,或者是設計者對自己設計產品的立場以及創作的理解,仍是滯后的——設計的遠景目標是消費,而消費的形態是“日常生活”,其主體是作為接受者的人的欲望。
2
文學中的“細節描寫”是決定敘事真實及具有感染力的常用技巧。無論主題是否宏大,反映日常生活的“細節”是思想的血和肉,“細節”真實的背后,是無法“篡改”的生活邏輯。現代主義的先驅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說過:“包括藝術,也應該殫精竭慮捕捉日常生活場景。”[2]就是這個意思。藝術并非純粹的藝術,而是源于日常生活的,那些戲劇與文學,本身的土壤正是日常生活,這大概就是“無邊的現實主義”[3]的意思。那些所謂精英、草根的日常生活,也只是在反思層面的超越性不同,而對于日常生活本身來說,并無本質的區別。十年前,我在《“設計史”的本質——從工具理性到“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中談到法蘭克福學派以及當時的一些批判,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即認為工具理性或技術理性本質上是統治的合理性,是組織化的統治原則。工具理性或技術理性的發展導致主體的客體化、物化,并最終扼殺了文化的創造性、豐富多彩性,使文化成了一種工業文化、單面文化。[4]而在后現代思潮中,從對“日常生活”研究所產生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思想,實際上也已不屬于傳統美學范疇,而是指向一種更廣闊和更具有包容性的思考問題的方法。[5]
也正是由于日常生活與周遭的一切發生著即時的關聯,在今天,工具理性和日常生活審美化的關系有了模糊化的趨勢。工具理性更多地介入到了日常生活審美中,以至于工具理性本身也成為審美的一部分。典型如標準化,它把設計的功能主義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不但方便人的使用以及技術或零件的更新,形成更廣地域的服務和支持系統,同時也極大降低了成本,使得人人均可平等廉價地享受新技術的成果。
日常性呈現出一種非理性的敏銳性和先進性,“風起于青萍之末”,社會許多領域的大變革起源于日常偶發。例如當代技術與傳統手工之間的真實關系,當理論界還在討論工業技術是否構成對手工藝術的損害的時候,很多年輕一代的手工藝人,早已借助新的技術與工具開展創作。在木雕創作中,用數字化精雕或者3D雕刻可以制作出非常好的基礎作品,再經過手工修改和打磨,不僅提高了完成效率,而且便于不同體量的復制。人工智能技術雖然不能完全取代手工,但它強大的學習能力和延伸出的制作能力,與精湛的手工可以無限接近,并在降低基礎工藝等條件中,留出更為廣泛的創作空間。在機械復制時代或電子時代,工具理性的掌握者,具有一定的技術門檻和專業性,需要所謂的專業者來承擔。但在今天,技術門檻在消解,專業的界限也在模糊,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通行證)實質是區塊鏈網絡里具有唯一性特點的可信數字權益憑證,是一種可在區塊鏈上記錄和處理多維、復雜屬性的數據對象,它在藝術品的交易流通中,開啟了全新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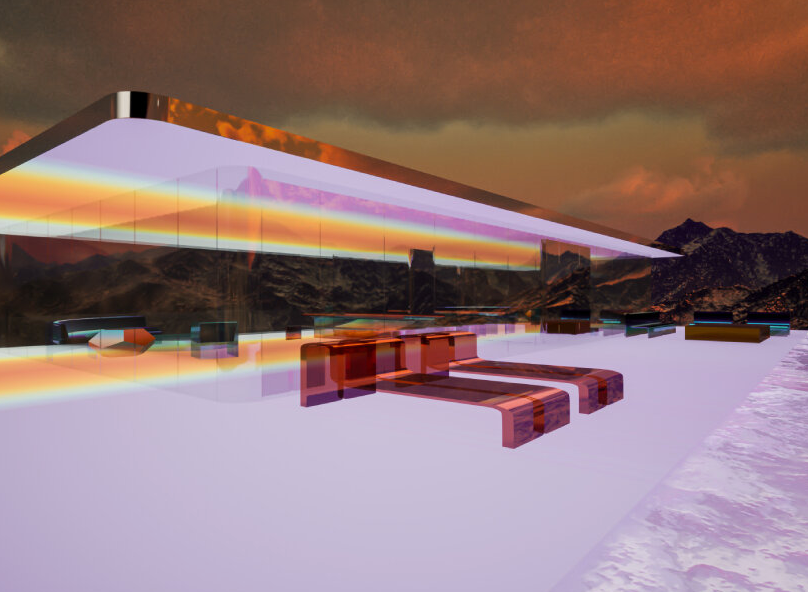
當代生活中,無論是普通人還是某一專業人員,在龐大的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所建構起來的技術平臺面前,基本上是平等的,像過去那樣的技術壟斷很難產生。隨著對技術應用場景的發掘,把既有的各種技術整合,也會產生創造性的概念,并重塑日常生活。在人工智能時代,一些傳統的工作出現了AI替代人類的可能,但工具理性時代的這種權力的消解,以及在日常生活審美化中對于各個階層之間的模糊和彌漫性,都會在相當長的時間中存在。
技術和藝術對社會生活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包豪斯時代已開始探討,第二任校長漢內斯·邁耶(Hans Mayer)與格羅皮烏斯的理性全然不同,他是一位激進的理想主義者。在1926年發表的《新世界》一文中,他談了在新技術影響下對未來世界的展望:“只要我們不以工程師的先入之見來解決城市建設問題,我們就會通過對廢墟的崇拜和走街串巷的思想來破壞現代城市的迷人生活。這個城市是最多樣化的生物聚集區,必須由人有意識地控制和建設。我們今天的生活需求在層次或變化上是相同的。一個真正的集體最可靠的標志是用同樣的方式滿足對平等的需求。這種集體需求的結果便是標準產品。”“對于當今經濟生活的半游牧民族來說,住房、衣著、飲食和心理需求的標準化帶來了重要的行動自由、經濟效率、簡化和放松。我們的標準化水平是我們共同經濟的一個指標。……新的藝術作品是一項旨在為所有人服務的集體作品,而非收藏家的個人對象或特權。”[7]烏爾姆學校則在對包豪斯進行批判的同時,自身也深陷于設計、科學和技術間不確定的關系之中。烏爾姆過于強調技術、工業化特征、科學的設計程序,而忽視了人的基本心理需求。之后,歐美那些著名的藝術和設計學院,以及思辨設計或批判式設計的思想,都希望更好地解構現實,試圖在當代科技和觀念之下,為生活價值以及在更廣泛的生態組合中定義自己。
“人類世”概念的提出,是設計研究者、設計師和策展人尋求提高對“人類世”認識時,強調對這些實踐者所發展的敘述保持批判。什么是“人類世”?荷蘭化學家和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在2000年使用該詞后,“人類世”(Anthropos=human, cene=new)一詞被許多研究領域所采用。“人類世”認為人類已經進入一個新的地質時代,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可見的和持久的影響。由于人類世的命名是為了揭示今天世界生態危機的根源,因此再提出的觀點中都試圖更直接地指向造成最大生態破壞的人類活動的途徑。安東尼·鄧恩(Anthony Dunne)菲奧娜·拉比(Fiona Raby)夫婦在他們的《思辨一切》(Speculative Everything)一書中解釋了為什么他們稱自己的作品為“設計”,而不是“藝術”。他們說:“我們希望藝術令人震驚且極端。關鍵設計需要更貼近日常生活:這就是它干擾的力量所在。”[8]2011年我在負責首屆北京國際設計三年展策展時,鄧恩夫婦是我們遴選的“可能的世界”部分的策展人,他們當年這樣闡釋自己的策展理念:“批判式設計采用投機性的設計方案,挑戰人們對產品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狹隘假設、成見和觀念。它是一種態度、一種立場,而不是一種方法。”[9]這表明,批判式和思辨性的設計作品,其目的是關于我們如何與技術和科學相聯系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在政治和社會組織結構中,以及如何在更廣泛的生態組合中定義自己的方法和角度。也因此,批判性設計在當代設計發展新的階段上,成為全球化問題境遇下重要的聚焦點。

回顧法蘭克福學派關于新工具的論點,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是相對存在的關系,價值理性的實現,必須以工具理性為前提,雖然工具理性中也包含有物質形態的工具與精神形態的工具。這一點在設計中表現得尤其明顯,設計從來都不僅僅呈現為單向度的物質功能屬性,而通過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思辨或批判,使設計呈現超越工具理性的面貌和復雜性。



